|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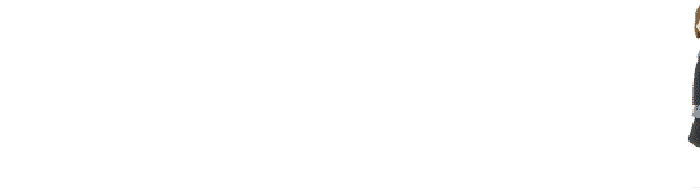
|
加利看見狗向自己撲來,轉身就逃。每一咬,每一抓,都意味著死亡。他向門廊,向門廊後面屋裏的那片安全世界逃去。但他喝過太多的酒,在火爐邊度過太多太長的冬日,在草坪椅上度過太多太長的夏夜。他可以聽見庫喬在後面靠近了,然後是一段可怕的短暫瞬間,他什麼都沒聽見,他知道,庫喬撲起來了。
他的一隻腳剛踏上門廊前正在剝裂的第一級臺階時,聖 伯奈特狗兩百磅的重量像一節火車頭那樣擊中他,隨著一陣風的呼嘯,他被擊倒在地。那只狗向他後頸撲來,加利喘著氣爬起來,狗壓在他身上,下腹的毛幾乎要讓他窒息,它已經輕而易舉地把他仰面撲倒。加利尖叫了。
庫喬在他肩頭高處咬了一口,它有力的前爪抓過加利裸露的皮膚,挑出了筋,那些筋像一根根斷了的鐵絲。它繼續嗥叫。血流出來了,加利感到它們從上臂熱乎乎地向下流。他轉身揮動雙拳向狗連續猛擊,起了一點作用。加利手腳並用起身向前爬了三步。庫喬又撲來了。
加利一腳向狗踢去。庫喬向一邊虛晃一下,又徑直探身鑽入,嗥叫著猛撲過來、泡沫順著它的顎流下來,加利可以聞到他嘴裏的氣味,那張嘴腐敗、惡臭、泛著黃色。加利掄起左拳猛擊過去,拳頭擊中庫喬下頜的骨架上,打得正准。重擊的震動順著胳膊傳向他的肩,肩頭被深深咬開的那個傷口火辣辣地疼著。
庫喬又退開了。
加利看著狗,他沒有毛的胸部上上下下急促地動著,臉變成了灰色,肩頭的撕口裏滿是血,血又濺落到剝落著的門廊臺階上。“向我撲過來,你這野種。”他說。“過來,撲過來,我連屁都不會放一個。”他尖叫著,“你聽見沒有?我連屁都不會放一個!”
但庫喬又退了一步。
這些話仍然沒有什麼意義。但恐怖的氣味已經離開了這個男人,庫喬不能肯定是不是要再次出擊。它受傷了,那麼悲慘地受傷了,這世界成了這樣一種感覺和印象的碎料縫成的花被褥——
加利一搖三晃地站起來。他倒退著上了門廊的最後兩級臺階,肩頭的感覺就像有桶汽油澆進了皮下。他的意識對著他語無論次地喊:“狂犬病,我得了狂犬病。”
沒關係,一次一個,他的獵槍就在廳中的壁櫥裏。感謝基督的愛,布萊特 坎伯今天離開了,沒有在山上。這都是因為上帝的仁慈。
他找到紗門把手,把門拉開。他雙眼緊盯著庫喬,退進門裏把它關上。他感到一種巨大的解脫,他的腿有了彈性。有一瞬間世界遊走了,但他伸出舌頭狠狠地咬了一下,又把自己拽了回來。現在他沒有時間像小女孩那樣神魂顛倒,只要他想,可以在狗死了以後再那樣做。但上帝,它就在外面,他想他肯定只有一路戰鬥著才能出去了。
他剛轉身順著黑暗的走廊走向壁櫥,庫喬就撞碎紗門的下半部分的擋板沖了進來,它的鼻吻從牙齒前向上翻著,像在輕蔑地笑,一連串沒有生命的狂吠從它的胸中發了出來。
加利又尖叫起來,他迅速轉身,庫喬撲過來時他的雙手正接住了它。他被從廳的一邊撞到了另一邊。
加利喘著氣掙扎著想要站穩,有一刻,他們像是在跳華爾滋,然後加利(他輕五十磅)倒了下去。他隱約感覺到庫喬的鼻吻伸到了他的領下,隱約感覺到庫喬的鼻子噁心地幹熱。他掙扎著舉起手,想著庫喬咬住他的喉嚨要把它撕開時,他要用拇指戳向庫喬的眼睛。他的尖叫聲中,庫喬又殘酷地攻擊了他。他感覺熱乎乎的血濺滿了他的臉,心想,親愛的上帝,是我!他的手輕輕打中庫喬的上身,沒有產生任何結果,然後它們落了下去。
隱約中,他聞到了金銀花的香氣,噁心而膩味。
“你在看什麼?”
布萊特向他母親聲音的方向轉了過去了一點,沒有全部轉過去,他一刻也不想錯過沿途連綿的景色。
公共汽車幾乎在公路上開了一個小時,他們已經通過百萬美元大橋進入南波特蘭(布萊特瞪著兩隻迷惑、好奇的眼睛看著港口的那兩艘裝鐵渣餅和鏽鐵桶的運貨船),匯入向南的收稅快速幹道,現在正開向新罕布什爾州的邊界。
“每一樣東西,”布萊特說。“你在看什麼,媽媽?”
她想,玻璃中你的影子——非常模糊,我就是在看你。
但是她回答說,“當然,這世界,我想,我看見這世界在我們面前鋪展開來。”
“媽,我真希望我們能乘著這輛車一路開向加利福尼亞,我們就可以看見地理書上寫的每一樣東西。”
她笑起來,摸著他的頭,“你看景色已經看得太累了,布萊特。”
“不,不,我不會。”
可能地不會,她想。突然她感到沮喪,感到自己老了。星期六早上她打電話給霍莉問她他們能不能去時,霍莉很高興,她的喜悅讓沙綠蒂感覺自己還年輕。奇怪的是自己兒子的喜悅,他幾乎顯而易見地異常地興奮,讓她覺得自己老了,然而
他究竟會變成什麼樣一個人?看著他那張像是通過某種攝影技巧重疊進一路變幻著的景色裏的幽靈一般的面孔,她這樣問自己。他聰明,比她聰明,比喬聰明得多。他應該上大學,但她知道,他上高中時,喬會施加壓力讓他註冊手工藝和汽車維護課,這樣他可以在修車鋪裏更好地幫他。十年前他不可能有機會這樣幹,因為指導老師不會允許一個像布萊特這樣聰明的孩子只選手工藝行當的課程,但是在當今這種學校裏充斥著階段選修課,老師們都大喊“做自己的事”的時代,她非常擔心這種事會發生。
這讓她害怕。她曾經能夠告訴自己——離上學還遠著呢,所以離上中學,真正的學校,還非常遠著呢。小學對幹布萊特這樣動輒會從課堂裏溜出去的男孩來說,只是一個玩的時期。但到了中學,很多不可逆轉的抉擇就要開始了,很多門會輕滑地鎖上,那種輕微的卡塔聲只有幾年後在夢裏面才能聽見。
她緊抱著雙肘,微微有些顫抖,甚至沒有欺騙自己這是因為灰狗空調的溫度開得太高了。
布萊特離上中學只有四年了。
她又一次顫抖,突然間發現她在惡意地希望自己從沒得過那筆錢,或她丟了那張票。他們離開喬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但從1966年她和喬結婚以來,這是她和他第一次分開。
她還沒有意識到前景會那麼突然,那麼令人頭暈目眩,那麼痛苦地出現。看著這樣一幅畫面:女入和男孩被從城堡的拘禁中釋放出來……但仍有一種感覺重重地壓在他們心頭,釘在他們背上的是大鉤子,系在鉤子另一端的是看不見的重型橡皮帶,未及你走遠,情況說變就會變,你又會被啪地一聲拉回去,一下又是十四年。
她的喉嚨發出一種怨艾的聲音。
“你說了什麼嗎,媽?”
“沒有,只是清了清嗓子。”
她第三次顫抖起來,這一次她的胳膊上起了雞皮疙瘩。她想起自己上中學英語課時學過的一首詩(她曾想過要去學大學的課程,但她的父親聽到這種想法時怒氣衝天——一她是不是認為他們有錢?——她母親也憐憫地輕輕笑起來)。那是迪蘭 湯瑪斯的詩,她已經記不清整首詩的內容了,但大致記得它講述的是在愛的毀滅中的遷徒。
當時那行詩只讓她覺得有趣和困惑,但她想她現在可理解它了。如果不是愛,你還會把那種不可見的重型橡皮帶稱之為什麼呢?難道她還想欺騙自己說,即使是現在,她並非在某些方面愛那個與她結婚的男人?她和他在一起難道只是出於一種責任,或只是為了孩子(真是一種令人痛苦的笑話。如果她離開他才會是為了孩子)?難道他在床上從來就沒有讓她快樂過?難道他不能有時、甚至是在最難料到的瞬間(比如說剛才在汽車站上時)對她溫柔?
然而……然而……
布萊特望著窗外,怔怔地出神,他問:“你覺得庫喬會沒事嗎,媽?”他仍看著窗外的景色,沒有轉過身來。
“我肯定它會很好。”她心不在焉地說。
她發現自己第一次在考慮離婚的細節——怎麼做才能養活自己和兒子,他們怎樣度過這種不可想像(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局面,如果她和布萊特旅行後沒有回家,他會不會像在波特蘭含糊不清地威脅過的那樣來追他們?會不會通過某種體面的或骯髒的手段帶布萊特回去?
她開始在腦海裏列舉各種可能性,衡量它們的輕重,她突然發現,對未來的一點點考慮,畢竟不是件壞事。痛苦?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有用。
灰狗越過州分界線,進入新罕布什爾州,向南駛去。
三角洲727飛機在陡峭地爬升,折向羅克堡上空——這種時候,維克總是想找到靠近城堡湖和117道的自己的家,總是毫無結果——然後又向東海岸飛回去。這是一次飛向洛報機場的二十分鐘的飛行。
多娜和泰德在一萬八千英尺下麵。他突然間感到一陣沮喪,混雜著一種黑色的預感——要出問題,他們甚至發瘋地希望出問題。當你的房子倒了之後,你只有重建一幢新房子,你沒有辦法用埃爾瑪膠把舊房子再一次粘起來。
一位空姐走過來。他和羅格正在一等艙(“能享受時不妨享受一下,老夥計。”羅格上星期三訂票時曾說,“不是每個人都能乘一等艙去討飯的。”),機艙裏還有四、五個其他乘客,多數都像羅格一樣在看報紙。
“請問您要些什麼嗎?”她問羅格時,臉上帶著一種很專業的燦爛的微笑,好像每天單調的生活——早上五點三十起床,然後上上下下地從班戈起飛,到波特蘭,到波士頓,再到紐約——總能讓她感到大喜過望。
羅格心不在焉地搖搖頭,她又帶著那種聖潔的微笑轉向維克,“您要什麼,先生?甜圈?桔汁?”
“能不能給我快點調一份桔計酒?”維克問,羅格的頭啪地從報紙上抬起來。
空姐依然微笑著,乘客早上九點前要一份飲料,對她來說不是什麼新聞,“我很快就可以調好一杯。”她說.“但您訪快一點喝,波士頓馬上就要到了。”
“我會儘快。”維克鄭重地答應了。她於是離開他們,去了廚房,這位微笑的空姐,穿著一身深藍條制服,顯得那樣燦爛伯人。
“你怎麼啦?”羅格問。
“你什麼意思,我怎麼啦?”
“你知道我什麼意思。平時晚上五點前你都不喝酒,不到中午更是滴酒不沾。”
“我正要開船出海。”
“什麼船?”
“皇家遊輪泰坦尼克號。”
羅格皺起了眉頭,“這個玩笑的品味很糟糕,你不這樣認為?”
是這樣,事實上就是這樣。對羅格這種人本該好好……。但這個上午,壓抑仍像塊惡臭的毯子般緊緊地裹著他,他實在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他沒有發火,只是努力做出一個相當淒涼的笑。但羅格仍只是沖著他皺眉頭。
“羅格。”維克說,“對於活力穀這件事,我有了一個主意。它會像一條母狗那樣逼得夏普老先生和‘小孩’就範,不管你喜不喜歡,它大概確實行得通。”
羅格看起來松了一口氣。這是他們之間經常能行得通的一種工作方式:維克想出粗略的概念,羅相讓概念得以成型、實施。當要把概念揉進各種媒體,或他們要做概念介紹時,他們總是這樣組合起來工作。
“怎麼做?”
“給我一點時間。”維克說,“可能要到今晚,那時我們就可把它升上旗杆——”
“——就可以看出是誰脫了褲子。”羅格做著鬼臉幫他說完。他打開報紙,又開始看金融版。“好,那麼今晚我就會知道了。夏普的股票上星期又長了八個點,你知道嗎?”
“非常好。”維克喃喃自語。
窗外,霧已經消退,天空非常晴朗,肯尼幫克海灘、奧貢魁克海灘和約克海灘,構成一張天然全景畫明信片——深藍色的是海,卡其黃的是沙灘,遠處有緬因州低緩的山丘,開闊的草場,和沿綿向西一往無垠的茂密的冷杉林帶。真美!但無限的美景,只是讓他更加壓抑。
如果我要哭,我一定要去廁所裏哭。他倔強地想。一張廉價紙上的六句話就能讓他變成這樣,這真是一個脆弱的世界,脆弱得像外面塗成燦爛的五彩,裏面卻空無一物的復活節雞蛋。就在上周他還在想是不是帶上泰德一走了之,現在卻擔心起他和羅格回來時,泰德和多娜會不會還在家。有沒有可能多娜帶著泰德跑了,也許就去了她波科諾斯的母親家了?
當然可能。她可能覺得分離十天還不夠,對他也不夠,對她也不夠,也許分居六個月更好。現在她有了泰德。根據法律分割財產的原則,她就可以多占幾個點,不是這樣嗎?
而且可能。一種聲音爬動著,悄悄鑽進他的腦子。可能她知道坎普在哪里,可能她決定去找他,和他試著過一陣,他們會一起回憶快樂的過去。現在我腦海裏有一個非常瘋狂的想法,他很不自在地告誡自己。
這種想法不肯離去。
飛機在洛根機場著陸時,他終於喝完了最後一滴桔對酒,這讓他的肚子裏直發酸。他知道,這種感覺會和多娜,和斯蒂夫 坎普一起緊緊地纏住他一個上午,即使他吃了一大碗可哥熊,它還會一點點爬回來——但心中的壓抑減輕了一點,也許,這也值得。
也許。
喬 坎伯迷惑地看著大老虎鉗夾具下的那一塊車庫地板。他把綠毛氊帽向前額推了推,又向那兒看了一會兒,然後把手指放進嘴裏,吹了一個響哨。
“庫喬,嘿,孩子!來,庫喬!”
他又吹了一個響哨,彎下腰,兩手捂著膝。狗會回來,他不懷疑這一點,庫喬從來不跑遠。但他該怎麼處理這件事?
庫喬在車庫地板上拉了泡屎。
他從來沒有想到這條狗會這麼做,它還是條小狗時,也從來沒有這樣幹過。它小的時候在附近撒過幾泡尿,小狗們有時會這樣幹;它也曾狠狠地咬過一兩次椅子的坐墊。但從來沒有發生過今天這樣的事。他也懷疑過是不是其他的狗幹的,但這忡推測很快就被推翻了,因為據他所知,庫喬是羅克堡最大的一條狗。大狗吃得多,拉得也多。沒有什麼長卷毛狗、比哥獵狗。或漢茲五十七代變種之類的狗能弄出這麼一大團來。喬懷疑庫喬是不是嗅出了沙綠蒂和布萊特要出去一段時間。如果是那樣,也許這是它表達自己看法的一種方式。
這只狗是他1975年一次修車活的報償。那個顧客是北面弗賴伊堡附近一個叫雷 克羅威爾的獨眼龍。克羅威爾平時在林子裏工作,但人們知道他很懂狗性——他很會養狗,也很會訓練狗。本來他可以幹新英格蘭鄉下所謂的“牧狗”業,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但他的脾氣不太好,他總慍怒,這趕走了很多顧客。
“我的卡車需要一個新的發動機。”那年春天,克羅威爾告訴喬。
“行。”喬。
“我手頭有馬達,但是付不出勞務費,我把錢輸光了。”
他們站在喬的車庫內,爭執不下。布萊特那時只有五歲,他正在院子裏無所事事地晃悠,他的母親在晾衣服。
“那太糟了,雷。”喬說,“但我不為人白乾,這兒不是慈善機構。”
“比斯莉夫人剛生了一個小子。”雷說。比斯莉夫人是一條上等的聖 伯奈特母狗。“是純種,你給我幹這個活,我把那個小患於給你。你覺得怎麼樣?不過你得先幹,沒有卡車我就沒法運木材。”
“我不需要狗。”喬說,“尤其是一條那麼大的狗,一條該死的聖 伯奈特狗就是一台吃飯機器。”
“你不需要狗,”雷說,他看了一眼布萊特,布萊特正坐在草上看母親,“但是你兒子可能喜歡一隻。”
喬的嘴張了張,又合上了。他和沙綠蒂不需要看家狗。但自從有了布萊特之後,他們沒有再要過其他孩子。從布萊特出生到現在,已經有這麼長時間了,有時看著這個孩子,喬腦子裏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他孤獨嗎?可能是,也許雷 克羅威爾是正確的,布萊特的生日就要到了,他可以送他一條小狗。
“我會考慮考慮。”他說。
“好,不過不要考慮得太長。”雷說,他有點生氣,“我還可以去北康威找文 卡拉翰,他的手藝也像你一樣好,坎伯,可能比你還好。”
“可能。”喬說,他很平靜,雷 克羅威爾的脾氣沒有讓他吃驚。
同一個星期,一家超市的經理開著一輛雷鳥來找喬。車的變速裝置壞了,只是個小問題,只要排幹液井,重新把它裝滿,再上緊了傳送帶,就基本差不多了。
但他修的時候,這個叫多諾凡的經理在一旁小題大做地咕叨來哈叨去。這輛雷鳥很棒,它是196O年造的,到現在幾乎還像一輛新車。活快幹完的時候,喬聽見多諾凡說他的妻子希望他賣了這輛車。喬有了個主意。
“我想給兒子買一條狗。”他一邊把雷鳥從千斤頂上放下來,一邊說。
“噢,是嗎?”多諾凡禮貌地問。
“是的,是一條聖書奈特狗,現在它還是只小狗,但長大後它就會吃得很多。現在我在想,我們兩個能不能做一筆交易。如果你能答應折價賣給我幹狗食,比如說蓋恩斯碎穀粉。拉斯頓一普林那,或你賣的任何類似的東西,我可以保證你每次開雷鳥過來時,我都給你檢修一下,不收勞務費。”
多諾凡很高興,他們倆握手談成了。喬打電話給雷 克羅威爾,說如果克羅威爾仍然同意,他準備接受關於那只小狗的交易。克羅威爾同意了。這一年布萊特過生日的時候,喬把一隻一刻不停地扭來扭去的小狗塞到兒子的懷裏,這把布萊特和沙綠蒂都驚得目瞪口呆。
“謝謝你,爸爸,謝謝你,謝謝你!”布萊特叫了起來,擁緊爸爸,在他面頰上吻了個遍。
“好小子。”喬說,“但是你要照看好它,布萊特。它是你的拘,不是我的。要是我發現它四處拉屎撒尿,我會把它帶到穀倉後面,當做條野狗一槍幹掉。”
“我會的,爸爸……我保證。”
他一直努力信守諾言,做得相當好,也有很少時候他沒有做到,沙綠蒂和喬就會默不出聲地把狗弄髒的地方清洗乾淨。後來喬發現,對庫喬袖手旁觀已經不太可能,它長大後(而且它長得真它媽快,很快就變成喬預想的那種吃飯機器了),已經完全成了坎伯家的一員。它長成了一條忠實的好狗。
庫喬很快就養成了居家生活的各種好習慣……但現在?喬轉了一圈,雙手塞在褲子裏,皺起了眉頭。周圍沒有一絲庫喬的影子。
他走出去,又吹響了口哨。這該死的狗可能正在山下的小溪裏避暑。喬不會罵它,現在屋裏陰涼的地方也有八十五度。但那條可惡的狗會很快回來,只要它回來,喬就會把它的鼻子塞進那灘臭哄哄的東西裏面讓它也聞個夠。如果庫喬是因為沒有找到人照看它才這樣幹的,喬懲罰它時心裏會很難過,但是你不能讓一條狗養成一種僥倖——
喬想到一個新問題,他用手掌輕輕拍著前額,他和加利走後誰來喂庫喬?
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穀倉後那個喂豬的飼料槽裏填滿蓋恩斯碎穀粉——他們住宅下的地窖裏還有大約一長噸那種東西。但如果碰上下雨,它們會不會浸透?如果他把它們堆進屋裏,庫喬進屋後可能就會對準門也拉一大泡屎。另外,說到食物,庫喬是一個胃口極好的貪婪的傢伙,它會第一天吃掉一半,第二天再吃掉一半,然後餓著肚子四處亂竄,直到喬回來。
“狗屎。”他喃喃道。
狗沒有來。他大概是知道喬會看到那一攤東西,害怕了。作為狗,庫喬是一條聰明的狗,知道(或猜出)這種後果,不會超出它的智力範圍。
喬找到一把鏟子,把那攤東西鏟走,然後潑上一些他留在手頭的工業清潔劑,把汙跡擦掉,最後從車庫後面的水龍頭打來一桶水,把那塊地方徹底清洗乾淨了。
幹完後,喬拿出一本螺旋線裝邊的小筆記本,裏面是他的工作日程表。他創覽了一下,裏奇的國際豐收者已經幹完了——用鏈吊把馬達吊出來容易得就像取一根胸針。他推遲變速器的活沒有遇到什麼困難,那個教師就像預料到地那樣好說話。另外還有五六件活,都是小活。
他進了住宅(他從來沒打算費勁在車庫裏裝電話,他曾告訴過沙綠蒂,他們會為那根額外的線向你收取高價),開始打電話給有關的人,說他因為生意上的事,要離開小鎮幾天。他應該能及時趕回來,這樣他們不至幹帶著問題開上很長的路去找其他人修,如果誰的風扇傳動輪或散熱片軟管壞了,汽車熱得不行,就對熱的地方撤泡尿。
打完電話,他又進了穀倉。走前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一個換油和上環的活。車主說好午前來取車,喬必須要工作。他想,沙綠蒂和布萊特走了……庫喬也走了,這個宅子有多麼靜。通常,那只碩大的聖 伯奈特狗會趴在車庫大滑動門後的陰影裏,一邊喘著氣,一邊看著喬幹活。有時喬會對他說話,庫喬看起來總像是在仔細聽著。
被拋棄了,他很有些憤憤地想,被他們三個都拋棄了。看了一眼庫喬拉過屎的地方,他搖了搖頭,既厭惡又迷惑。他又想起該怎樣喂這條狗的問題,但滿腦空空。好了,待一會兒給老佩爾維爾打一個電話,也許他能想出某個人——某個小孩——可以在這幾天上山來喂庫喬。
他點點頭,把收音機調到挪威WOXO台,把音量放高。除了播出新聞或球類比賽的結果時,他並沒有在認真聽。現在是工作時間,尤其是每個人都不在,他必須要工作。住宅裏的電話響了一、二十遍,他沒有聽見。
上午,泰德在自己的屋裏玩玩具卡車。在人世間的四年裏,他已經收集了三十多輛小卡車,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這其中有七十九美分的塑膠車,那是他父親從藥店買來的,維克總在星期三晚上去藥店取《時代》雜誌(玩那些七十九美分的汽車時,你必須小心,因為它們是臺灣製造的,容易摔壞)。這一系列小機器的首領,是一輛到他膝高的黃色大湯加推土機。
他有各種“人”可以放進卡車的駕駛室裏。有些是他從玩校玩具中搜出來的圓臉的傢伙,另外一些是士兵。不少是他所謂的“星球大戰裏的人”,包括盧克、漢 索羅、帝國惡人(又叫達斯 威德)、一名貝斯平戰士、還有泰德絕對最喜歡的格雷多,格雷多總是開湯加推土機。
有時他用卡車玩危險的大公,有時是馬丁和熊,有時是員警和非法釀酒者(他的爸爸媽媽帶他去挪威露天影院看過一次雙片電影——白閃電和白線熱,那兩部片子給泰德的印象非常深),有時,他玩一種他自己想出來的遊戲,叫做十卡車掃蕩。
但他玩得最多——也是他現在正在玩的——沒有起名。它包括把卡車和“人”從他的兩個玩具箱裏一個個挖出來,把卡車一輛輛地在他的小屋裏斜排成平行線,把“人”放進去,好像它們斜停在一條只有泰德才能看見的大街上。然後他會非常慢地把卡車一輛輛開到另一道牆的牆根,仍是一輛緊靠著一輛,車仍和牆根成著斜角,然後再換一邊。有時他會不知疲倦地玩上一個多小時,排十到十五遍。
這個遊戲給維克和多娜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著泰德一遍遍地排那種一成不變、幾乎是典儀式的佈局,有時也很煩心。他們都問過地,究竟覺得這種排列有什麼吸引力,但泰德找不出適當的措辭來解釋。危險的大公、員警和非法釀酒者以及十卡車掃蕩,都是簡單的撞擊——毀滅遊戲。那個無名遊戲卻平和、寧靜、有秩序。如果他的語彙量足夠大,他可能就會告訴爸爸媽媽,這是他說“阿姆”的方式,他就這樣打開了冥想和內省的心靈之門。
他現在正在玩這個遊戲時,他在想,有什麼事出錯了。
他的眼睛自動地——毫無意識地——轉向了衣櫥的門,但問題不在那裏。門緊緊地鎖著,自從有了“惡魔的話”以後,它再也沒有打開過。不,問題在其他地方。
他不能確切說出是什麼東西出了問題,也不能肯定他自己是不是真想知道。和布萊特 坎伯一樣,他也能明白地讀懂地漂浮於其上的那條父母河的流淌。就在最近,他感覺那條河裏有黑色的漩渦,有沙洲,可能就在表面下還暗藏著陷講;他感覺那裏有急流,瀑布,有任何東西。
他的母親和父親之間有問題。
問題在他們相互看著的方式上,在他們相互交談的方式上,在他們臉上,在他J臉下,在他們的思想裏。
他把斜停的兩行卡車一輛接一輛排到房間的一邊,然後上樓。他去了窗口邊。地玩這個沒有名字的遊戲已經有了好一會兒,膝蓋已經開始疼了。
下面的院子裏,母親正在掛衣服。半小時前她曾給一個男人打過電話,那個男人能修那輛品托車,但他不在。她等了很長時間,希望聽見有人說“你好”,後來她重重地把電話掛了,幾乎要氣瘋,媽媽以前從沒為一件這種小事氣成那樣。
他默默地看著,母親已經掛上了最後兩張床單,她看著它們……她的雙肩有些下陷,然後她走到雙股曬衣繩外的蘋果樹前,站在那兒,泰德從她的姿態——她的腿伸著,頭低著,雙肩微微地抽動——看出,她在哭。他看了她一會兒,離開了窗口,又回到他的卡車旁。他覺得胃裏有一個空塊,他想父親,非常想他,但這讓他更難受了。
他又慢慢地推著那些卡車穿過房間,一輛接著一輛,又回到那種斜停的行。紗門砰地響了一下,他停下來,心想,她會叫他。但她沒有。
有腳步聲穿過廚房,大臥室裏她的那張椅子吱吱呀呀也響了一下,她坐下了。但電視機沒有開。他想她只是坐在那兒,只是……坐……他很倉促地把這些想法清出了自己的腦子,想要把它們徹底清除乾淨。
他排完了汽車列隊。格雷多,他最好的那個,坐在推土機裏,茫然地從他那雙圓圓的黑眼睛中望出去,他在看泰德的衣櫥。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他在那裏看見了什麼,好像是某樣駭人的東西驚嚇得他把眼睛睜得火大的,某個真正危險的東西,某個可怕的東西,某個正在到來的東西——
泰德心神不寧地看著衣櫥,它緊緊地鎖著。
他已經對這個遊戲厭倦了。他把卡車放回玩具箱裏,很響地關上,希望她能知道他已經準備好下樓去看八頻道的《硝煙》。他站起來走向門口,又停下,轉眼看向“惡魔的話”,入迷了:
“惡魔,遠離這間屋!
這兒沒你的事。”
他默記著它們。他喜歡看它們,強記它們,看他父親的手跡:
“這一整夜,沒什麼可以碰泰德,或傷害他。
這兒沒你的事。”
在一陣突然、巨大的衝動下,他拔下了把那張紙固定在牆上的按釘。他小心、幾乎是恭恭敬敬地把“惡魔的話”取了下來。他把這張紙折起來,又小心翼翼地放進牛仔褲後面的口袋裏。現在他的感覺比一天中的其他時間都好了。然後,他跑下樓去看《馬竭爾 迪龍和弗斯特斯》了。
最後一個人十二點差十分到了,取走了他的車。他支付了現金,喬把這筆錢塞進油膩的舊錢包裏,提醒自己和加利離開前要到挪威儲蓄所再取五百塊。
想到要離開,他又回想起了庫喬由誰來喂這個問題。他鑽進福特車,再到了山腳下的加利 佩爾維爾家。他把車停在汽車道上,抬腳走向門廊前的臺階,一聲招呼已經升到了他的喉嚨眼,在那兒,它消失了。他退下去,彎腰看那幾級臺階。
臺階上有血。
他用手指碰了碰,血已經成了膠狀,但還沒有完全幹。他又站起來,有一點憂慮,但還沒到心急如焚的程度。加利可能喝醉了酒,手裏拿著個玻璃杯摔了一跤。但緊接著,他就看見了紗門鏽跡斑斑的下底板上被撞開的那個大口,他真正擔心了。
“加利?”
沒有回答。他發現自己開始懷疑,是否有什麼心懷嫉恨的人來找老加利?或者,是否有什麼旅遊者來問方向,加利糊裏糊塗地告訴他,他可以飛起來和月亮交配?
他上了臺階。門廊的地板上濺著許多血,更多的血。
“加利?”他又叫了一聲,突然間他很希望右肩頭沉沉地壓著他的那技獵槍。但如果有什麼人把加利一拳打飛出去,打得他的鼻子血肉模糊,或最後幾顆老牙都跳了出來,這個人應該已經走了。因為院子裏除了喬生了鏽的福特LTD車外,就是加利的66型白色克萊斯勒硬頂車。誰也不會走著去3號鎮道——加利 佩爾維爾家離小鎮有七英里遠,離通回117道的楓糖路也有兩英里遠。
更可能是他自己割開了自己,喬想,但天哪,我真希望他割開的是他的手,而不是他的喉嚨。
喬打開紗門,它的鉸鏈在吱吱呀呀地響。
“加利?”
仍然沒有回答。空氣中有一種有點噁心的甜味,讓他不太舒服,他想,這大概是金銀花的香氣。他左邊有一條樓梯通向二樓,正前方是廳,廳盡頭的走道通向廚房,廳右邊的中部也何一條走道,它通向臥室。
廳中間的地板上有個東首,但周圍太暗,喬看不清楚。它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撞翻了的茶几之類的東西……但喬知道,加利家的前廳並沒有放什麼傢俱,一直就沒有。下雨的時候,加利把草坪傷搬進來靠在廳邊上.但已經有兩個星期沒有下雨了。而且,那些草坪椅現在就在加利的克萊斯勒車旁,緊靠金銀花叢的老地方。
但這氣味並非來自金銀花。它來自血。一大攤血。那個東西也不是翻倒的茶几……
喬快步走到那個形狀前。他的心在哈哈地跳,他在它旁邊跪下,一種短促的尖聲從他身上發了出來。突然間屋裏的空氣變得非常熱,非常窒息,像有人正在把他往死裏扼。他離開加利,一隻手捂在嘴上,有人謀殺了加利,有人——
他強迫自己向回看。加利躺在自己的血泊裏,他的一雙瞎眼瞪向天花板,他的喉嚨開了,不只是開了,仁慈的上帝,它看起來像是被嚼開了。
這一次他的咽喉沒有再做任何掙扎,他只是讓每一樣東西隨著一連串絕望、窒息的聲音出來。幾近瘋狂之中,喬意識的後背帶著一種孩子氣似的怨恨轉向沙綠蒂。沙綠蒂旅行去了,而他卻不能。他不能,因為某個瘋了的混蛋對可憐的老加利 佩爾維爾駭人聽聞地下了毒手——
——他必須報告警方。不管其他事怎麼樣,不管老加利的眼睛怎樣在黑暗中瞪著天花板,不管他的血的氣味怎樣地和金銀花讓人噁心的甜味混在一起,他要報告警方。
他站起身來,挪動雙腿搖搖晃晃地跑向廚房。他在喉嚨深處嗚咽著,自己卻不知道。電話就在廚房的牆上,他必須打電話給州員警署,班那曼長官,或其他什麼人——
他在門口停住了,眼睛開始睜大、最後幾乎要從腦袋裏面進出來。有一隻大狗小山一般蹲在通向廚房的走道口……從那座山的大小他已經知道了那是誰家的狗。
“庫喬。”他低聲說,“噢,我的天,庫喬瘋了!”
他聽見後面有一種聲音,迅速轉過身去,他的頭髮纏結著從脖子後飛揚起來,但後面空空如也……只有加利,那個幾天前的晚上還說喬不可能趕庫喬去咬一個叫著的黑鬼的加利,那個喉嚨口被撕開一直撕到後脊樑骨的加利。
冒險是沒有意義的。他突然轉身沿著走道沖出去,他有一腳踩到了加利的血裏,其後的一個很長很長的瞬間裏地滑了一下,在身後留了一個長長的血腳印。他的喉嚨又嗚咽了,但當他關上重重的內門時,他感覺好了一點。
他又轉過身,向裏看,只要庫喬在那兒,他隨時準備把廚房門口的門關死。他的意識又一次在遊走,他又一次渴望右肩頭有那種背有獵槍的沉重感。
庫喬不在廚房裏,除了窗簾偶爾在窗外吹進的微風中輕輕地擺動,屋裏一片寂靜。有一些陳年的伏特加酒瓶子,散發著酸臭的氣味,但比那種……其他的氣味好一些。
陽光照在退了色的油麻氈上形成一種奇怪的圖案。電話還掛在老地方,它原本白色的塑膠盒,現在已經在老光棍不知多少頓飯的油的浸漬下變得灰暗,很久以前老酒鬼跌倒時留下的裂痕還在它表面。
喬進來,把門在身後關緊。他經過兩扇開著的窗時向外看了看,後院的陰影裏除了加利以前用過的兩輛鏽跡斑斑的破車躺在那兒,就再也沒有其他東西了。但他還是關上了窗。
他走向電話。在這間悶熱的廚房裏,他的汗幾乎在向下傾瀉。電話簿由一根草繩拴著就掛在一邊。穿草繩的眼是加利一年前用喬的鑽孔機打上去的,老醉鬼當時還醉熏熏地說他連屁都不會放一個。
他拿起電話簿,但它又掉了下去,砰地打在牆上。他的手感覺非常沉重,嘴裏有一種嘔吐後混濁、污穢的味道,他又拿起電話薄,重重地翻開,重得幾乎要扯下書皮。本來他可以撥0或555-1212,但震驚之中,他已經把這些都忘了。
喬的呼吸聲、急促沉重的心跳聲和翻動電話號碼本簿時發出的嘩嘩聲,淹沒了他身後一種輕微的響聲——庫喬用鼻子頂開地窖的門時發出的輕輕的響聲。
咬死了加利 佩爾維爾後,它就下了地窖。廚房裏的光線太強烈、太眩目,把白熱的痛苦如同堅硬的鋼片一般插向它正在腐敗的腦子。地窖的門微開著,它搖晃著下了臺階,進入那一片天賜的黑涼世界。它躺在加利的老軍用床腳箱旁,幾乎要睡著了。窗外來的微風幾乎要把地窖的門關上了,但還沒有鎖住。
喬的嗚咽聲、幹嘔聲、哈哈地跑過廳,又砰地關掉前門的聲音——把它再一次從痛苦中打醒。它痛苦,沉悶,無休無止地暴怒。現在它站在喬身後門口的黑暗中,頭低著,眼睛近乎血紅,黃褐色的厚毛上纏結著血塊和未幹的淤泥。
喬在書中查到了羅克堡。他找到C開頭的文字,他的一隻手顫抖著順著頁面滑到某一欄中用小框框出的羅克堡市政服務,也就是行政司法長官辦公室。他伸出一隻手指開始撥號。正在這時,庫喬胸中深深地發出一聲嗥叫。
喬 坎伯身體裏的所有神經幾乎都要跳了出來,電話簿從他手裏滑下來,又砰地一聲打在牆上,他慢慢轉向那個噙叫的聲音。他看見庫喬站在地窖的門口。
“好狗子。”他沙啞著嗓子低低地說,唾沫順著他的兩頰流下來,尿浸濕了他的褲子。刺鼻的氨臭衝擊著庫喬的鼻子,像是狠狠地打了它一個嘴巴。它撲了起來。喬像踩著高蹺一樣斜避向一旁,狗狠狠地撞在牆上,牆紙撞破了,泥灰“噗”地飛濺出來,形成一片白色的沙氣,庫喬沒有嗥叫,一連串沉重。刺耳的聲音從它胸中發出來,這聲音比任何叫聲都更兇殘。
喬退向後門,一把廚房倚在他腳下絆了一下,他發瘋般晃著雙臂要保持平衡,但庫喬已經打上來沉沉地把他壓在身下。這個一身血紋的殺人機器,一串串的白沫從它嘴裏向後飛著,一種新鮮、濕軟的惡臭包圍著它。
“噢,上帝,它壓到了我身上!”喬 坎伯發出驚叫。
他想起了加利。他用一隻手蓋住咽喉,掙扎著用另一隻手抓向庫喬。庫喬向後退了片刻,它的眼裏冒著火花,鼻吻向後翻著,又露出那種兇狠、沒有一絲幽默感的咧嘴,它露出的牙齒,像是一排泛著黃色的剛硬的籬笆尖。然後它又撲了過來。
這一次,它撲向了喬 坎伯的睾丸。
|
|
|
|